摘要: “学院派—2015·青年水墨展”7月初将亮相李可染画院美术馆。“学院派”作为一个展览题目是我们笼统地对参展水墨艺术家“学院”身份的一种强调,并非归纳提炼一种艺术风格。
原标题:“学院派”—2015·青年水墨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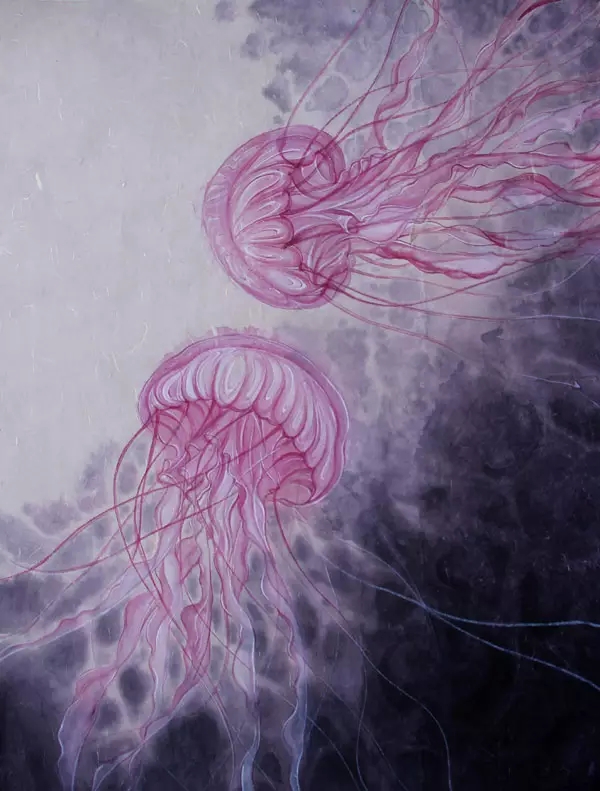


这项议题,或者说是价值取向点来源于中国现代艺术教育中“学院”的历史情境与问题。回望过往,现代艺术教育中“学院”在中国的诞生、发展是与中国社会机制的转变、文艺思潮的碰撞、价值观念更迭相呼应的。1906至1910年间,两江师范学堂、保定优级师范学堂、北洋师范学堂等官办教育最早设立的图画手工科,便是将国人观念中的“技艺”进行“学院”化的早期过程(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这是中国艺术现代化必要进程,从艺术史角度来说,它应是传统技艺向“艺术”的观念转变过程),这种尝试是在“实业救国”的思潮中产生的。尽管当时的教学模式谈不上一点学院规范,只是将传统师徒模式搬进了学堂,然而它却代表了一种对西方科学精神的向往,而这种科学性恰恰代表着一种学院精神;后来,随着周湘、刘海粟、徐悲鸿、颜文樑等一批留学生回国创办的各类美专,如上海美专、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等等,才真正将中国的艺术教育推向了专业化、学院化:艺术课程设置、教学相对系统化、完整化。当时,学院的教学内容与机制主要是借鉴了日本、法国的西画教育模式,由于日本的西画教学又是受西欧法国的影响,因此中国早期的学院化教学是法国“学院派”体系的一脉,这应是中国艺术学院教育第一次与所谓的“学院派”、“学院主义”发生关系。
然而,有意思的是法国高度成熟的学院派风格体系却没有在中国的学院里“生根发芽”,这大概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中国风起云涌的社会革命、民族战争所造成动乱局面并没有给当时的学院派教学留出“生根”的时间与空间;二是中国早期艺术院校的设置以及后来的发展似乎证明,其机构的宗旨似乎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相对独立、规范、科学的艺术教育机构,而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想与态度的实践场所,如很多艺专早期大多是本着设计实用的思想而创建的,后来随着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美育”思想的推行而发生走向(国立杭州艺专是当时实践蔡元培美育思想重要阵地),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建国前各大美术学院重新调整,包括后来教学改革中对油画、国画的改造,年连画系设置等,“学院”的发展几乎被中国社会的各种人文思潮所捆绑。正所谓有所失必有所得,艺术学院的发展尽管被各种力量所裹挟,无法形成西方学院通过严谨性与客观性教学体系建立体来的稳固性,但这种脆弱性却赋予了中国后来学院教育中兼容并包的精神特性。从学院艺术的发展来看,二十世纪前半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种社会机制的瓦解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让萌芽中的艺术学院始终处于一种活跃与流动的状态,这种“活跃性”无法形成固定、统一的审美趣味、审美话语机制,自然也就不能形成如法国那样代表皇家审美趣味的“学院派”,然而这种活跃性却作为一种艺术的内在特质,如血液般融化在艺术学院中,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艺术学院是全世界最有活力,也最为外界奇怪的地方——学院中既存在大批的写实画家,也有思想叛逆的当代艺术家,而且有时候他们甚至合二为一,艺术家并非人格的分裂,而是艺术风格的兼容。
建国后,中国的社会政治机制一度通过美术院校的合并,美协、画院机构的设置来规范学院的审美趣味及机制,并且也从苏联契斯恰科夫素描体系以及苏联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找到了一条中国学院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就是中国后来八十年代学“学院主义”的雏形。从教学模式的系统化、完整性来看,这个“学院主义”主要存在形式是油画,雕塑其次;尽管当时学院里的国画、年画、连环画也在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下,甚至参与人数更多,但是由于国画、年画、连环画这个创作群体没有相对科学的教授体系,只是学院教师、画家、工农兵群众相对个人化的创作模式,而与通过引进苏联体系化的现实主义创作无法相提并论。五、六十年代“学院主义”的早期成果主要是派遣苏联的留学生以及苏派专家马克西莫夫油训班等一批学生创作的革命现实主义历史画,如罗工柳的《地道战》、冯法祀《刘胡兰就义》、何孔德的《出击之前》等等,但后来随着中国与苏联关系的破裂以及后来一系列政治运动,这种创作方式并没有走向深入,直至改革开放后随着靳尚谊等一批美术教育家在艺术视野与绘画实践上的成熟才真正产生了中国的“学院主义”,即新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作为西方观念意义中的“学院派”,它首先克服了新中国第一代油画家在油画创作上的缺点,真正从西方油画中找到了一条造型与用色的写实主义的创作模式,这种创作模式也主导了国画、雕塑等其它艺术门类的创作,反应在国画领域则是徐悲鸿、蒋兆和及其师生建立起来一种“写实主义”的国画。由于,中国画与西方艺术存在造型与审美语言的差异,国画一直就涌动着现代学院教育体系与传统审美体系的矛盾与冲突,这也是建国初期各地纷纷成立立地方画院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新古典主义在学院内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八五新潮”现代主义如火如荼的时期,各种艺术观念充斥在学院内外。学院既成为新古典主义的温床,同时也是前卫艺术的实验场地,其中尤以中国美术学院与中央美术学院最值得关注。
如培养了杨飞云、朝戈、王沂东等新古典主义画家的中央美术学院,也同样孕育了徐冰、吕胜中、隋建国、展望、方力钧、刘小东等一批“亦正亦邪”的学院艺术家,而引人思考的却是后者。这批学院出身的当代艺术家,他们受教于八十年代,接受的正是严格的、规范的学院主义的训练;单从这批艺术家的职业发展路径来看,他们最初获得学院认可的正是他们突出的学院体系化创作,这些可以从他们学生时代的毕业作品中寻找到端倪,然而他们并没有满足于学院的现状,而是将思想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各种思潮中,在现实社会的生活中找到了艺术创作的灵感。尽管学院体系作为一种艺术机制可能对他们的艺术创作形成了某种“束缚”,但也正是这种“束缚”,让他们在“反束缚”的艺术创作中脱离出“学院”、“教师”的角色,而成为一位“学院艺术家”。其中,“反束缚”的核心正是当代大学教育所贯穿的对“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培养,这似乎也是对上世纪前半期兼容并包的学院精神一种延续。
翻阅这些史实,其实主要是为了说明:在中国,学院不等于“学院主义”,百年的学院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一套严谨、规范的学院机制与模式,这是现代学院走向科学化、规范化的必然结果,而这种“科学性”并非机械、僵化的创作机制,而是一种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视野;与此同时,学院也不仅仅代表一种艺术价值,也是一种思想精神、文化立场,中国艺术学院自身的历史与问题已表明我们需要用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变动的世界。
这才是我们此次展览所要呈现的,“学院派”作为一个展览题目是我们笼统地对参展水墨艺术家“学院”身份的一种强调,并非归纳提炼一种艺术风格。因此,在展览作品中既有立足于学院造型语言对技术进行传承的传统之作,也有笔墨创新的实验作品;但是他们这个群体艺术家之所以称为“学院派”,就是他们在思想上绝非为了商业而商业,也不完全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一种带有个人文化立场与价值判断的艺术探索。我姑且将之归结为“学院精神”,即在自由、开放、独立的思想基础上,对学理与文脉的一种传承与创新。
转载旨在分享,文章、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进行删除。
请扫描新闻二维码
加载更多+